蒙古的全面南侵与南宋的绝地反击:长江在燃烧
金国的轰然倒塌,让南宋朝野,尤其是以赵范、赵葵兄弟(时任两淮制置使)和全子才(时任淮西制置使)为代表的激进主战派,血脉贲张。他们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蒙古主力北撤(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中原空虚,一举收复故都东京汴梁(开封)、西京洛阳(河南府)、南京归德(商丘)等“三京”之地!实现“据关(潼关)守河(黄河),光复祖宗基业”的宏图。
郑清之力排众议(以史嵩之为首的务实派强烈反对,认为蒙古必报复,且后勤难继),在理宗的支持下,批准了入洛计划。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宋军兵分两路:
-
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自庐州(合肥)出发,一路几无抵抗,于六月十二日“收复”汴梁。然而,这座梦寐以求的故都,早已是“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一片废墟。更致命的是,军粮告急!
-
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自泗州北上,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后,不顾粮草匮乏的现实,强令部将徐敏子、杨谊等率军西进洛阳。七月,宋军前锋进入洛阳,同样是一座空城、死城,“城内并无一物,遗骸遍地”。此时,宋军已断粮多日,“采蒿和面作饼而食”。
蒙古人并非毫无防备。窝阔台大汗震怒于南宋的“背信弃义”(蒙古视中原为其征服之地),立即命大将塔察儿(国王)率机动部队南下,并令在河南的游骑袭扰宋军粮道。同时,蒙古军掘开黄河寸金淀(开封附近)水淹宋军后勤路线。宋军粮道彻底断绝!
七月末,塔察儿部主力进逼洛阳。缺粮疲惫的宋军被迫在洛阳城东三十里处的龙门(今洛阳南)迎战。蒙古铁骑如潮水般冲击宋军阵线。宋军虽奋勇抵抗,杨谊部先溃,导致全军动摇。一场惨败,主将徐敏子身负重伤,仅率残部数百人浴血突围南逃。洛阳得而复失。东线的赵葵、全子才在汴梁听闻洛阳败讯,又遭蒙古游骑不断袭扰,加之粮尽,军心崩溃,只得于八月仓皇放弃汴梁,全线南撤。
“端平入洛”以彻底的惨败告终。宋军损失精锐数万(主要是西进洛阳的部队),大量物资器械丢弃,寸土未得,反而彻底激怒了蒙古,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提供了完美的借口。消息传回临安,“更化”的光环瞬间黯淡。主战派声望扫地,郑清之引咎辞职(后被复用,但影响力大减)。主和(实为务实备战)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然而,一切都太迟了。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大会,正式决定发动对南宋的全面战争!蒙古帝国这台战争机器,轰然启动,矛头直指南宋。
1235年春,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正式决议发动对南宋的全面战争。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如三支淬毒的利箭射向南宋:
-
西路军(皇子阔端、大将塔海等): 主攻四川,意图夺取天府之国,顺长江东下。
-
中路军(窝阔台三子阔出、大将口温不花、塔思等): 主攻荆襄(湖北),目标直指南宋长江中游的防御核心——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
-
东路军(宗王口温不花、察罕等): 主攻两淮(安徽、江苏),威胁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门户。
四川的炼狱:成都之殇(1236年)
西路军阔端部势如破竹。1236年正月,蒙古军攻破蜀北门户沔州(今陕西略阳),守将高稼力战殉国。九月,蒙古骁将按竺迩率精锐骑兵长驱直入,突破南宋在蜀口(秦岭通道)的层层防线,兵临成都城下。此时的成都,承平日久,城防松弛,知府丁黼虽奋力组织抵抗,奈何兵微将寡,援军断绝。
蒙古军架起回回炮,巨大的石弹呼啸着砸向城墙,砖石崩裂,烟尘蔽日。城破之时,蒙古骑兵如潮水般涌入,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繁华的锦官城沦为地狱,“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昭忠录》所载,数字或有夸大,但惨烈可见一斑)。丁黼在两名副将的保护下,按照预定的线路,向南门撤退。行至西南四五里地,来到金花街菜园地,被蜂拥而来的蒙古军四面包围,乱箭横飞。丁黼被数箭穿心,当场阵亡。此时已是天交四鼓,即二十日凌晨。成都失守,蒙古军进城。丁黼虽然阵亡,但目睹他临敌无畏的部下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参议官(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王翊带着残部一直与蒙古军进行惊心动魄的肉搏巷战。十月二十六日,蒙古军冲进知府衙署,发现官厅里面空荡荡的,一位身着整齐朝服的官员正襟危坐在大厅中央。蒙古军丢下王翊,在城里“纵火大掠”,王翊眼看百姓受到伤害而无力救助,便纵身投井。天府之国的心脏被狠狠刺穿,四川全境震动,残破不堪。此乃南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败。
荆襄的砥柱:孟珙的“机动防御大师”(1235-1240)
中路蒙古军(阔出为主帅)的目标是荆襄。这里是长江中游的锁钥,襄阳若失,则江南门户洞开。然而,蒙古人在这里遭遇了南宋真正的战神——京湖制置使孟珙。
孟珙,名将孟宗政之子,深谙荆襄地理与蒙古战法。他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多层次、大纵深、机动灵活的防御体系:
-
三“海”联防: 在核心区域(江陵府周边)大规模兴修水利,形成三道以湖泊、河流、沼泽、堰塘构成的广阔水网防御地带(称为“三海”),有效迟滞蒙古骑兵。
-
星罗棋布的堡垒: 在要冲之地广筑堡垒(如枣阳、光化、信阳等),互为犄角,屯驻精兵。
-
精锐的机动兵团: 组建强大的野战部队(如“忠顺军”),由孟珙亲自指挥,哪里危急就驰援哪里。
1236年,蒙古名将塔思(木华黎之孙)率军猛攻江陵(荆州)。孟珙坐镇江陵,先派出小股部队多路袭扰,焚烧蒙古军粮草,使其疲惫。同时,他亲率主力在江陵外围布防。当蒙古军逼近时,孟珙命令部队在江陵城周围广布疑兵,点燃无数火堆,绵延数十里,夜间烽火相连,照耀江面如同白昼! 蒙古军远道而来,见宋军声势浩大,阵势森严,疑有重兵埋伏,军心震动,竟不敢深入,被迫撤军。孟珙“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保住了长江中游重镇。
1237年,蒙古军转攻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孟珙再次发挥其机动防御的精髓,迅速调集兵力支援,内外夹击,大败蒙古军于光化城下。1238年,孟珙更是主动发起反攻,成功收复了此前被蒙古占领的襄阳、樊城、信阳、光化等战略要地!这是南宋在全面防御战中取得的最辉煌的攻势胜利,一举稳定了荆襄战局,孟珙因此功升任京湖、四川宣抚使(后改制置使),成为南宋西线战场最高统帅。 在他的经营下,荆襄防线成为南宋最坚固的屏障。
东线:血火两淮与杜杲的安丰奇迹(1235-1241)
东路的蒙古军由口温不花、察罕等率领,主攻两淮。这里是南宋的财赋重地和京畿屏障,防御体系最为严密(依托淮河、长江及众多堡寨)。
1237年冬,蒙古大将张柔(汉人世侯)率军攻陷南宋淮西重镇光州(河南潢川),打开了通往淮西的门户。随后,口温不花、察罕率主力围攻淮西另一要害——黄州(湖北黄冈)。黄州知州孟珙(此时已调任京湖,但黄州属其防区)再次展现出卓越的防御才能。他亲自坐镇,指挥军民死守,并利用水军优势不断袭扰蒙军。激战数月,蒙古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围。
1238年秋,蒙古军转攻淮东,目标直指庐州(合肥)。守将杜杲(时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早已严阵以待。杜杲是南宋著名的守城名将。他加固城防,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鹅梨炮、三弓床弩等守城利器。蒙古军架起数百座巨型抛石机(回回炮)猛轰庐州城,昼夜不息,城墙多处坍塌。杜杲指挥军民,用木栅、盛满沙土的布袋(“木女头”、“布袋阵”)甚至熔化的铁汁(“金汁”)堵住缺口,并组织敢死队趁夜出城反击,焚毁蒙军攻城器械。庐州城在血火中屹立不倒,蒙古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主帅察罕也被炮石击伤,被迫撤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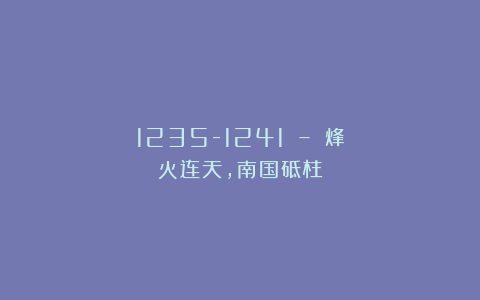
窝阔台之死:欧亚大陆的震颤与长江畔的喘息(1241年秋冬)
当杜杲在安丰城头擦拭着溅满血污的鹅梨炮,当孟珙于江陵府衙中对着荆襄地图凝思破敌之策,当余玠在合州钓鱼山督建新城墙时,一股源自万里之外、足以撼动整个战局的巨大冲击波,正穿越草原与山河,向东亚大陆袭来。
狩猎行帐中的骤逝:
1241年冬十一月(具体日期史料记载不一,有十一月初五、初七、初八等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在和林(哈拉和林)附近的一次盛大狩猎(或宴饮)后,猝然崩逝于行帐之中,享年五十六岁。《元史》等记载其死因或与“饮酒过量”有关。这位在位十三年(1229-1241)、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横扫东欧)和灭金、侵宋战争的大汗,其生命如同草原上最猛烈的风暴,在巅峰时刻戛然而止。
权力真空与帝国刹车:
窝阔台的突然离世,瞬间在蒙古帝国的权力核心层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和真空。按照蒙古传统,新大汗必须通过全体宗王、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推选产生。此时:
-
继承人之争暗流涌动: 窝阔台生前属意其孙失烈门(其子阔出早逝),但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以及威望卓著且手握西征重兵的拔都(术赤之子)等,都对汗位有着潜在的诉求或影响力。复杂的权力博弈即刻展开。
-
前线统帅的羁縻: 正在指挥攻宋的三路大军统帅,如阔端(窝阔台次子,西路)、忒木䚟(中路)、口温不花、察罕(东路)等,皆为宗王或与黄金家族关系密切的重臣。汗位更迭的敏感时期,他们必须关注后方的政治动向,甚至可能被召回参与拥立新君。继续大规模、高风险的前线作战变得不合时宜。
-
乃马真称制与战略收缩: 在忽里勒台大会召开前,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依据蒙古旧俗“称制”,暂时摄理国政。她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稳定内部。面对复杂的继承形势和可能的内耗风险,乃马真后以及蒙古核心贵族们达成共识:暂停对外大规模征服战争,尤其是进展并非一帆风顺的南方战线(南宋)。一道紧急命令从中枢发出:前线各路军队,除必要留守部队外,主力停止进攻,相机后撤或就地转入防御,等待新汗继位后的决策!
长江畔的意外喘息:
这道来自遥远和林的罢兵令,如同久旱后的甘霖(尽管充满不确定性),洒在了南宋浴血苦战的各个战场上:
-
四川: 阔端的主力在肆虐川西、川北后,本可能继续向川东、川南施压。罢兵令至,其攻势明显放缓,部分军队开始北撤。这给了余玠宝贵的时间窗口,得以在残破的蜀地更从容地推行其山城防御体系,加固钓鱼城、青居城等要塞。饱受蹂躏的川民,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喘息,得以掩埋尸骸,重建家园。
-
荆襄: 中路蒙军在孟珙的顽强抵抗下,虽仍占据襄阳等部分要地,但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忒木䚟等将领接到命令后,停止了对江陵、鄂州等核心区域的压迫性攻势,转为小规模袭扰和巩固占领区。孟珙敏锐地捕捉到敌军动向的变化,他利用这难得的间隙,加紧整修城防,补充兵员粮秣,并派兵收复部分失地(如1239年曾短暂收复襄阳,但因兵力不足旋得旋失,此时可加强控制周边),同时忧心忡忡地向临安上书,强调“虏虽暂退,其志未衰”,必须趁此良机,大修战备!
-
两淮: 东路蒙军在东口温不花、察罕指挥下,虽在安丰、庐州受挫,但实力犹存,仍对淮河防线构成巨大威胁。罢兵令下,其大规模攻城行动基本停止,军队收缩至几个主要据点(如光州)。淮河前线的警报级别暂时降低。杜杲等守将得以加固在战火中受损的城防,医治伤员,恢复生产。
临安的迟钝与余玠、孟珙的远见:
前线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喘息期,传递到南宋都城临安时,朝堂的反应却显得复杂而微妙:
-
“虏酋毙命”的短暂欢愉: 窝阔台死亡的消息传来,临安城内确实弥漫过一阵轻松甚至欣喜的气氛。一些官员将此视为天佑大宋,认为蒙古内乱将长久持续,威胁大减。
-
主和派的“安枕”论: 以宰相史嵩之为代表的主和(或务实派)势力,虽不至于完全松懈,但更倾向于利用此机会巩固现有局面,甚至尝试与蒙古方面进行接触(尽管效果甚微)。他们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内部财政、人事上。
-
主战派的忧虑与呐喊: 以杜范、刘晋之等为代表的清流官员,以及最重要的前线统帅孟珙、余玠,则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孟珙在奏章中痛切陈词:“和议不可恃,虏情叵测…今其内乱,正我卧薪尝胆、奋发自强之时!宜选将练兵,储粮缮城,以备不虞。若因虏乱稍息,辄生懈怠,异日祸至,悔之何及!” 余玠也在四川全力构筑山城体系,深知蒙古的威胁只是暂停,而非消失。
-
理宗的摇摆与错失的良机: 宋理宗赵昀在短暂的兴奋后,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他既希望享受和平,又害怕承担放弃备战的骂名。朝廷虽然也下达了加强防务的诏令,但在史嵩之的主导下,缺乏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倾尽全力的整军经武计划。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在临安朝堂的争论、地方执行的效率低下以及普遍的侥幸心理中,被一点一点地消耗。最为讽刺的是,当四川前线最需要支持以重建防御时,朝廷反而因“敌退”而削减了部分军费!
尾声:
1241年窝阔台的猝死,如同在宋蒙战争的血色长卷上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
它让蒙古帝国这台恐怖的战争机器,因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而被迫刹车。三路攻宋大军攻势顿挫,主力后撤或转入守势。
-
它给了南宋一个意料之外、苦苦挣扎得来的喘息机会。长江流域的烽火暂时减弱,前线军民得以从持续数年的高强度厮杀中获得片刻休整。
-
然而,这喘息并未带来新生。临安朝廷未能如孟珙、余玠所疾呼的那样,将其转化为厉兵秣马、彻底革新防务、扭转战略被动的黄金窗口。内部的党争、苟安的心态、资源的分散,使得南宋错失了可能是其后期唯一一次能系统性加强自身、争取战略平衡的机会。
-
暂停,不等于结束。 乃马真后的称制只是过渡,蒙古内部纵然有矛盾(如贵由与拔都的严重不和),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灭亡南宋的终极目标从未改变。一旦新汗(贵由)在争吵中勉强即位(1246年),或者更具雄才大略的蒙哥(拖雷之子)最终整合力量(1251年),那暂停的战争机器将以更凶猛、更高效的姿态重新启动。孟珙在江陵的忧虑目光,早已穿透暂时的平静,看到了那注定更加酷烈的未来风暴。
窝阔台饮下的最后一杯酒,暂时浇灭了南侵的烈火,却也在无形中,为南宋王朝敲响了更为深沉的暮钟。长江的呜咽,在短暂的停歇后,终将化为滔天的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