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汴京的秋夜总在子时转凉。欧阳修搁下笔,听见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翻动,像极了他少年时在洛阳见过的宫娥裙裾。那时的秋声是西京留守府里的捣衣声,一下下都敲在未央宫的铜壶滴漏上。而今夜的秋声更显清寂,檐角铁马叮咚,倒像是谁在叩打记忆的门环。
“初淅沥以萧飒”的风声,总教人想起江南的雨。欧阳修在夷陵任上见过这样的秋风,裹挟着长江的水汽,掠过秭归的橘林,将屈子祠的竹叶吹成满地碎玉。此刻的风却带着北地的粗粝,卷起汴河堤岸的柳叶,擦过宫墙时竟似胡笳十八拍的音节。他忽然明白,这秋声原是天地间的游吟诗人,用不同的方言在每个朝代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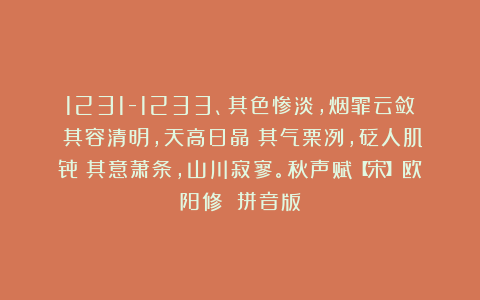
“其色惨淡,烟霏云敛”的意境里,藏着草木的私语。欧阳修在滁州醉翁亭听见过秋虫的合奏,纺织娘的银梭声与促织的铜钲音此起彼伏。如今这些声音都沉淀在《集古录》的拓片间,那些斑驳的碑文上,依稀可见前朝文人听秋时留下的泪痕。他伸手触碰案头的端砚,凉意渗入掌心,倒像是触摸到了时光的肌理。
“其气栗冽,砭人肌骨”的寒意,比江州司马的青衫更湿冷。欧阳修想起去年在扬州平山堂,见苏东坡将满地黄叶扫作”一蓑烟雨”的形状。那时的秋声还带着少年意气,如今却化作鬓角的霜色。他翻开《新唐书》的校样,墨香里竟混着汴京宫墙外的桂花气息,这让他想起韩愈《秋怀》里的句子,只是不肯说破。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的况味,最宜在夜航船上品味。欧阳修贬谪夷陵时,常在长江夜行,听橹声与雁阵共鸣。船过三游洞,水声激荡岩壁,竟似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在石缝间回响。此刻的秋声却近在咫尺,庭中老槐的落叶扑簌簌打在窗纸上,像是要把满腹心事说给案头的烛火听。
“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诘问,比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更苍凉。欧阳修摩挲着文忠公印,想起去年在洛阳见到的唐三彩,那些釉色斑驳的骆驼俑,驼峰间还残留着丝路的风沙。他忽然懂得,这秋声原是历史的和声,将魏晋的竹林风、盛唐的曲江雨、本朝的汴河月,都谱成了同一曲长恨歌。
当汴京的秋声漫过宫墙,欧阳修在《秋声赋》稿本上落下最后一笔。墨迹未干时,他听见儿子们在东厢房诵读《醉翁亭记》,童稚的嗓音里带着新笋破土的锐气。檐角的铜铃忽然轻响,惊起庭中宿鸟,扑棱棱的振翅声里,他看见自己的白发与月光融成一片银霜。这让他想起《周易》里的”穷则变,变则通”,只是嘴角的笑意尚未舒展,便被更漏声剪碎在五更的寒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