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美术的核心是反叛与实验,从形式探索到观念表达,从个体情感到社会批判,艺术成为不断自我更新的开放系统,这一时期的变革为当代艺术的无边界发展奠定了基础。
《豌豆花》
(Pea Blossoms) 1890年
油彩·布面 69 x 57 cm
私人收藏
波因特的作品展现出古典主义的严谨和典雅,画面构图均衡,线条流畅,色彩明净光润,代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艺术的巅峰。之前发表的100幅世界名画合辑中,展示的是波因特的《出水芙蓉》,本辑中更换为《豌豆花》。如果每一位画家只展示一幅代表作品的话,那波因特的这幅肖像画作品《豌豆花》必须是经典,只因朴实自然的美最能打动人心。
这幅画带我们走进了一位少女的静谧世界,女孩手捧一只小小的竹编花篮,满满一篮都是刚采摘的豌豆花。女孩身着带有小花刺绣图案的白色裙子,与头上淡金色发带相映衬,清晨的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女孩的眼神显得明亮而清澈,白色的花朵与少女的雪白裙装相互呼应,仿佛是她纯净心灵的延伸。背景中绿色的树叶青翠欲滴,豌豆花的清新被定格了,古典风骨里藏着对自然的深情,隔着画布观者都能闻到花香。在西方文化中,豌豆花常常与新的开始和纯洁的爱联系在一起,画中的豌豆花不仅是春天的象征,也寓意着重生与希望。
Gustav Klimt 奥地利
《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Ⅰ》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1907年
布面油画、金箔、银箔,140×140cm
纽约新艺廊博物馆,私人收藏
2006年,艺术界最轰动的新闻莫过于大藏家雅诗兰黛家族的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豪掷1.35亿美元(约10.76亿元人民币),将克里姆特的杰作《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Ⅰ》(又名《金衣女人》)收入囊中,这幅画被认为是克里姆特黄金风格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阿黛尔是糖业大亨费迪南·布洛赫·鲍尔的妻子,画面中的她身着装饰复杂的裙子,椅子与闪烁的黄金背景几乎融为一体,如同镶嵌在拜占庭风格的金碧辉煌之中。阿黛儿的头发、脸部、肩部与手均以传统油画手法绘制,与繁复的装饰形成鲜明对比。她两手交叠,表情迷离、忧郁而又放纵,形象似乎不属于尘世,带有一种浓厚的宗教与偶像气质。画作大量使用金箔,并融入了古埃及和拜占庭风格的抽象装饰元素,使得整幅画作显得既华丽又神秘。2015年上映的电影《金衣女人(The Woman in Gold)》完整记录了这幅画的离奇遭遇。
尽管克里姆特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热情狂放,但他的宇宙观却是叔本华式的:世界作为意志,是一股在无意义的生育、爱与死亡的无尽循环中的盲目能量,人生下来必将走向死亡,没什么可值得大喜大悲。因此,克里姆特的作品虽奢华且迷幻,但体现出的却是淡淡的哀愁与忧伤,透出一种严肃的氛围,无怪乎法国雕塑家罗丹观后,感慨地发出“深含悲剧性”的赞词。因此,将克林姆特简单地定位为「情色画家」是偏激且草率的。
纸醉金迷包裹下的静谧温柔、色彩繁华与内心困苦、具象与隐喻,每一对矛盾的树立与交融,都让不同时代的观赏者感受到这位奥地利画家的魅力:时而蕴含喜乐、爱慕、沉默与死亡,时而一派天真,却无损任何美的维度。或许对于他的风格,尼采的反讽一语中的:“过于深刻而显得肤浅。”语言的功能在浓烈的美与情感面前,总是捉襟见肘。
Henri Rousseau 法国
《梦》
(The Dream)1910年
油彩·布面,205×299cm
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New York),美国
“美丽梦幻中的亚狄维亚,朦胧中睡着了,弄蛇人袅袅的笛声,似乎萦绕在她的耳边,花丛与绿树之间,皎洁的月光正静静地映照。”这是1910年,卢梭的《梦》在独立沙龙展出的时候,画框上贴着的一首诗。
在一片开满各种奇花异朵和水果的热带丛林中,一位裸体的长发女子倚靠在深红色维多利亚式沙发上,这是卢梭初恋的情人。密林的一角升起了皎洁的月亮,一只禽鸟站在果树枝上,一动不动。密林中,两只狮子睁大了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前方和裸体女子。树丛间闪露出一只犀牛的眼睛,一个黑人正在吹奏竖笛,他漆黑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水乳交融,神秘的笛声似乎让所有的动植物都沉浸其中,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传达出潜意识中的未知和神秘力量。卢梭对这幅画是这样解释的:“沙发上沉睡的女人,梦见自己被运进森林,听着弄蛇人的音乐,这就是为什么画里要有沙发。”此时画家已经66岁,距离离开这个世界仅剩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梦,是画中女子的,也是卢梭自己的。
画如其人,卢梭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憨厚、乐观而又充满幻想的人,极致的苦难和极致的浪漫,都浓缩于其一身。他的一生贫穷而充满灾难,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相继离他而去,作品也一次次遭到沙龙的拒绝,甚至受到讥笑和嘲讽,一位巴黎的记者居然说:“卢梭先生是闭着眼睛,用脚在画画。”可是他从没有向命运和生活屈服,仍然大胆而又乐观地拥抱着新事物、新思想,用自己的画笔为生活而歌唱。当我们看过太多严谨而又精密的画作时,再看卢梭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趣,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憨朴、纯真、原始的气息,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更能触动人们心灵的深处。
亨利·马蒂斯 1869-1954
Henri Matisse 法国
《舞蹈》
(Dance)1910年
油彩·布面,260×391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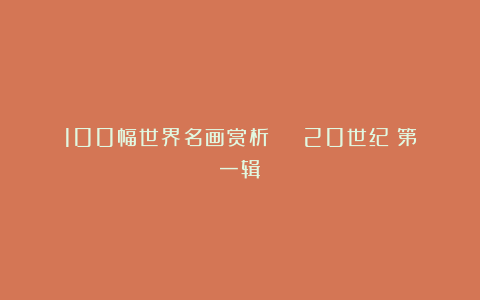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
20世纪初,艺术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野兽派”(Fauvism)作为一股新兴的艺术潮流,以其自由而大胆的色彩运用和简练的造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马蒂斯的《舞蹈》便是野兽派代表作之一。
马蒂斯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种流行于西班牙地区,名为沙达那的圆圈舞。画面中五个女子正围圈跳舞,只有左侧的人物在劲舞,而其他四个人物像失重一样的漂浮着,他们的动势因前方两人的手没有拉在一起而被打破。在色彩的运用上,蓝色、绿色、红色,三种颜色并置,共同建构了画面的组成,从而产生了一种原始感,马蒂斯用最饱和的蓝色塑造天空,用单纯的青绿色构造大地,用明亮的红色构造人体;线条运用上,全部采用曲线,与舞蹈欢愉的主题契合,使画面充满律动感;构图上,五位舞者占据整幅画面,甚至贴着边缘,仿佛舞台都承载不下他们的热情,进一步放大了想要表达的情感。
此画展示了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原始与魅力。画得像这个说法和他从来就没有关系,对此马蒂斯的回应是:精确描绘不等于真实。
马塞尔·杜尚 1887-1968
Marcel Duchamp 法国
《走下楼梯的裸女》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1912年
油彩·布面,147.8×88.9 cm
费城艺术博物馆,费城(Philadelphia),美国
1912年,一位名叫杜尚的青年将这幅名为《走下楼梯的裸女》的油画交到了一个由“立体主义者”举办的独立沙龙画展,主办方希望杜尚能把画作拿回去修改一下再来展览,可杜尚一言不发地把画拿走了。第二年,纽约举办了一场“军械库艺术展”,这场展览在美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奉为美国艺术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把杜尚引入到美国人的艺术视野,《走下楼梯的裸女》引发美国人开始质疑艺术的边界问题。
画中描绘的是气质优雅的裸女在旋转楼梯缓慢走下,这种行走的步调被画家划分为多个重影,从画面上可以大约见到五个人体,她们从画幅的左上方下来,右下角转身而去,其运动中扭动的躯干、臀、伸曲的腿、摆动的臂,构成一串由几何面穿插、叠印的轨迹。整幅画面的色彩比较单一,没有过多展现太多的对立因素。其实,还有一种解读,即我们在这幅画的画面中看不见什么裸女,也没有完整的楼梯,只能见到一些看来杂乱无章的线条。
《下楼的杜尚》曼·雷
《华尔街日报》则是这样评价的:“标题牛头不对马嘴,画布上没有裸体的人,不管你怎么用心看,也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都只能看到一块画布。”但是从这幅画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杜尚对于纯粹绘画语言的逐渐脱离,从用色到形体,到笔触的运用都充满强烈的立体派倾向。他将有关速度的连续信息归纳成整体来表现,造成了空间的“顿动”,使作品产生了主观能动性,并给予了观者体会作品的无限空间。
该作品遭到法国画展拒绝,这件事成为杜尚艺途的转折点。派系的争斗暴露出的人类本性的狭隘令杜尚大失所望,他从中看到了人类难以摆脱的利欲熏心的本性,从此不再相信人为的标榜,不再相信艺术是一方净土。
埃贡·席勒 1890-1918
Egon Schiele 奥地利
“绘画发出的光芒源于内在,他们自身就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并在其生命中显现,然后渐渐熄灭。”
—席勒
《死神与少女》
(Death and the Maiden)1915年
油彩·布面,89.5×125.5 cm
美景宫,维也纳(Vienna),奥地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这么一群人,忠于自我内心的情感,探索自我内在的精神,他们的艺术大胆、放肆、不受限制,忽视现实的形象,释放内心的欲望,忘情地扭曲与抽象,他们的艺术被定义为“表现主义”。
1918年维也纳第49届分离派的画展上,一名年轻的男子在展会上收到一封曾经的爱人沃利(Wally)的来信,信上除了诉说她对他的思念外,还有一张死亡证明。男子从容的收起信件,走到隔壁的房间里安静坐下,在展览宣传册的目录上,把曾描绘两人相拥的画作名字由《男人与女人》改为《死神与少女》。这个年轻人就是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此时维也纳分离画派创始人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也是他的老师,已在当年2月死于席卷欧洲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勒这时还不知道,死神不仅带走了他的前女友和老师,也很快会将他和他的妻儿一起带走。
埃贡·席勒与老师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死神与少女》堪称艺术史上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这幅创作于1915年的布面油画,捕捉了画家本人与情人沃利最后一次相拥的瞬间。死神以扭曲的姿态紧搂少女,而少女低垂的头部与空洞的眼神预示了悲剧的结局。席勒创作此画时,正值他决定抛弃沃利,迎娶中产之女伊迪丝(Edith)之际。沃利曾是他的缪斯与伴侣,却在席勒服兵役期间被彻底割舍。当她得知席勒结婚后,选择成为战地护士,最终因感染猩红热去世。席勒将“男人”改为“死神”,既是对沃利之死的忏悔,也暗示自己在这场爱情中扮演了“死神”角色。更具宿命感的是,席勒的妻子伊迪丝在1918年因西班牙流感去世,三天后,席勒也随她而去,年仅28岁。这幅画由此成为艺术家自身命运的预言。
画中的人物形象充满了病态、颓废、扭曲和痛苦的挣扎。他们仿佛在病痛中惊悸拥抱,在做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席勒本人的经历,敏感、痛苦和挣扎都深深地体现在他的画作中。当观者凝视这些作品时,或许会想起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话:“凡人是神的玩物,最光辉的生命也如落叶飘零。”艺术的意义,恰在于为这些飘零的瞬间赋予永恒的重量。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