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特:其实2024年那次个展上已经体现出那种转变了,已经没有那么平滑了。远看可能还是平滑的感觉,但你在离作品比较近的时候,能看到笔触,能看到很多绘画的痕迹,边缘线也不一定那么细致,这也跟我的工作方法的改变有关系。
AI:这些变化是怎么开始发生的,包括你开始强调笔触以及工作方法的转变,它们最初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傅斯特:是说我的创作是从哪里开始的吗?
AI:就是这些变化如何发生的?
傅斯特:这两种视觉的切换是怎么发生的吗?
AI:对。
傅斯特:直接来到问题的核心了,哈哈哈。我想想从哪开始说这个事儿,首先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工作方法的改变,它决定了你怎么去画,比如在之前那些比较平滑的绘画系列里,我是先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稿子,在把这个稿子变成绘画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更像一种写生。有了它作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参照之后,我可以在绘画的时候专注于笔触的处理,怎么可以更平顺,怎么能够更出效果、更有质感…可以更多地去思考表面的效果,它是否是吸引人的样子。我那个时候的画加了比较多的媒介剂,也可以说是一种湿接法,在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笔和颜色很润的,它的衔接就会比较creamy,比较自然,笔触衔接也比较顺滑。
现在的画法开始于是以一个相对来说不确定的状态往下推进,很多的形态、形象以及细节的塑造和它如何产生、如何改变,需要在过程中慢慢推敲。所以我的画法就变成了像是小碎笔在塑造的感觉,随时要用一些笔触给它破掉,再重新去弄,画法自然就发生了这种变化。
我在画这个过程中又感觉到了一种做雕塑的感觉,虽然我没做过雕塑,但我会想象做雕塑那种用小凿子在削、在切,一点点凿它,把一个平面的东西给凿成三维的感觉,它会慢慢地从一个大的切面到一个小切面,越来越小。你如果凑近我的画看,你会看到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俗称的“塑造”,这个真的是慢慢地推演出来的。
AI:工作室现在有没有过程中的作品可以看看?
傅斯特:这张就是未完成,我本来没想画这张,因为这张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参照,这是当我画了一半的一种感觉。
这个算是一个过程中的绘画,这边基本上是画了一遍的,那边画了两遍,第二遍的时候我自己不太满意,这张左右两边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因为左边还没画第二遍。
AI:这个程度再往前退一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傅斯特:就是第一遍铺色的时候,这个是铺了第二遍色。
AI:所以在一遍一遍的铺色中,那个笔触会更细?
傅斯特:它会有一些变化。你再看一下这张,虽然说画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痕迹可以看得到的。虽然说没有明显的笔触,但因为这个笔比较干,所以你还是能看到一些细微的笔触。
搬运者2
布面油画
160×130厘米
2024
AI:你更早的绘画我没有看过原作,只看电子图像会觉得像建模,现在的有点肉感,很像肉或别的软一点的东西。
傅斯特:对,它产生质感的过程也有一点偶然性,它有点像基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可以流动的一种状态。
AI:所以其实这种搞不清楚是固体还是液体的状态是你想追求的?
傅斯特: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刻意追求这种效果,只是我在画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以这种状态呈现是对的。这涉及到我如何定义我画的这些形象,它对我来说是什么?其实在一开始画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不会去想我要画什么,我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去构思一个系列或我要表达什么,它不是这样产生的。一般是在进行了一个阶段以后,我再去思考它的意义,或者这样的风格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可以试试的。这个系列总的来说有点像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不是一种通常的绘画。
我沉迷的那一点在于它像是我的一个造物一样,从无到有生成出来,它完全是一种“显现”的过程,正如上一次个展叫“赋形”,隐含有某种形而上的含义,它是一种可以任意变化的存在,所以它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的质感是流动性的质感。
AI:那你会避免它像什么吗?
傅斯特:是说确切的像,是吗?
AI:对,包括当中的某些局部,你画的时候会有感觉它们像现实中的什么物件吗?
眼前这幅,虽然颜色很淡,但它仍然给我那种很奢华的、腐朽的、盛极必衰的感觉。
傅斯特:你很敏锐。
AI:这是我直接感受到的。
傅斯特:腐朽和盛极必衰这种想法是我第一次听到。
AI:我看到这张画的右下角,实在太像一个肥胖女人的腿,我不知道你画的时候会不会避免让它像什么。
傅斯特:不会。我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比如说它有两个挺明显的卡通形象在这个抽象的身体里面,而且这两个形象好像情绪化地在进行一种互动的感觉,但是那个大的、具体的身体到底是什么?他是一个任意变化着的存在。它在这里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庞大身躯,因为过度的渴望“获得”而显得夸张的臃肿。我其实当时想呈现的就是这个臃肿的状态。它自己生长出的膨胀的、繁琐的、过载的东西。你把它想成一个胖女人倒也不违和。
AI:我很喜欢,我看着它会越想象越多。我记得有跟你分享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香港,眼前这个形象,甚至可以命名为“一个叫香港的女人”。
傅斯特:那种拥挤的状态?
AI:不是,我喜欢香港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发达过的地方,但现在有点衰败。发达过、下坡路、没有那么傲慢但你又可以足够相信它,相信它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即便如此狼狈,但你知道如果她能停下来,放下手中的重物喘口气,她仍然是一个值得你去交流的对象,因为她是见识过好东西的。
傅斯特: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好像跟你说过,这就是它的原稿,而且这原稿是跟波提切利的一张画有关系。而且这件作品我画了两个版本。包括我当时看了这张画的构图,它是三角形的构图,中间是这样一个最高的人,底下是一个袍子。
Lamentation over the Dead Christ
Sandro Botticelli
1490-1495
Tempera on panel
AI:波提切利的原画是表现什么的?
傅斯特:YS下十字架。我就是在看它的结构,它的整个构成,我就想我要画一个类似的构图。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要画一个单一的形象,这张画它其实产生于我这个系列第一二张的样子,就是类人形态系列的最初尝试。
AI:从这张原画到小稿,再从小稿到架上,你分别在做些什么工作?你是怎么思考的?
“搬运者”线描稿
傅斯特:首先我是从场景空间结构的构图出发,2023年以前我的大多数绘画都是在画空间性的构图,可能比较错综复杂的关系。空间里每一个部分之间的运动感比较强,或呈现相对静止,但它会是一个空间分布的状态,倾向于流动和离散感。后来就想画一个“人物”系列,打引号的“人物”,我尝试着在画一个聚合起来的形象。
这张就是一个尝试,我在看这样的构图的时候,尝试着用线描来去画这样的形象,当时没有任何的目的,只是在画的过程中扫一眼这个构图,我就开始用那种很细的铅笔在上面乱画。
AI:这些曲线其实都是你的手比较习惯的那种曲线。
傅斯特:对,它是一种画线的手感。在这一张画之前,我已经画了几本这样的线稿,所以已经开始建立起手感了,这一点对这个系列也挺重要的。
AI:这里有些曲线很像那些潮流艺术里面会出现的曲线,不是吗?
傅斯特:潮流艺术会用曲线吗?我以为潮流艺术只是一些特定的图像,我也不懂。
AI:我不确定,我是觉得这画面里面有很多小部件,如果拆出来的话感觉能拆出不少潮玩。
傅斯特:我倒不知道,不太清楚,哈哈。但你要说里边的卡通形象的话,可能是有些关系。不过关于卡通的话题,我们等会也可以聊一下。
AI:卡通是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东西吗?
傅斯特:它可以有关系,而且在某个阶段关系比较深,但不一定总有关系,它是根据某一个阶段我的推进需要出现的,包括这次群展里面有一张红色底子的,就挺明显有卡通的状态,而旁边的几件就不大有这种感觉。
我的系列一直是在流动的状态下往前推进的,在某个阶段我会尝试加入一些卡通的感觉,一方面能赋予这些抽象形态一种孩童视角的纯真有趣的感觉,另一方面是一种“游戏”的状态。而这也都跟我设定的这些figures的“本性”有关,也跟我自己的内在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是连接的。
另外还有几个比较明确的倾向,比如立体派、未来主义以及更早绘画的的影响。
AI:还有种壁画的感觉。
傅斯特:对,我确实也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也包括了那个时期的意大利湿壁画,你看我的书架上很多的书都是意大利的时期的绘画。这个系列最早开始的时候受到鲁本斯的影响。鲁本斯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艺术家,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线条”是核心的东西,我最先注意到的其实是“运动”感。
AI:我们上次聊到你搬回上海,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的选择。除了人际关系和生活圈子,回上海之后,在创作方面得到的反馈你能感觉到什么不一样吗?
傅斯特:在巴黎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直接得到很多反馈,因为作品出了工作室基本上就马上寄回国内,然后进行展览。如果说有反馈,就是间接通过画廊稍微获得一些反馈,他们也不一定会说特别多,也许最直接的反馈就是销售状况。也会稍微了解到藏家对作品变化的反馈,比如在24年以前和24年星美术馆这次个人项目以后,有些藏家喜欢那种变化带来的不一样,有的就喜欢以前的,甚至没再继续买了。但总的来说变化好像不是很大。
我其实挺期待这次回来能多跟我新认识的艺术家或者是能够碰到的藏家聊聊,主要也聊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让别人也先了解自己,我也想了解一下国内的艺术家不同的工作状态。
AI: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吗?
傅斯特:现在我其实接触的人还不是很多,你看我的工作室现在也才刚刚弄好,之前也挺动荡的,我自己也没有一直工作,还在慢慢安顿的状态。
AI:下个个展的大概时间现在确定了吗?
傅斯特:定下来了,明年3月在HdM。
AI:压力大吗?
傅斯特:压力还行,我有碰到过比这压力更大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自己还是可以应付的。
AI:你应该已经不太依赖感觉或者状态去作画了对吗?
傅斯特:状态是依赖的,我必须调整到一个好状态工作才能在一个轨道上,在那个状态下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
AI: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傅斯特:确切点讲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专注,不浮躁的状态。
AI:通常如果没在那个状态,是被什么事儿给打扰了?
傅斯特:最有可能是外部的事件造成的,内心的波动造成了状态上的波动。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做到完全屏蔽掉这些对我造成的波动。
AI:哪类事情更容易影响到你?
傅斯特:最近的我能想到的事情就是画廊出事的事情。
AI:那挺久了。你还会时不时感觉到它的影响吗?
傅斯特:不会了,现在离这个事情比较远了。所以我发现有些事你不去关注,它就远离你了,也不会来烦你,不会再产生那种烦扰。如果太把它当回事,反而它就会老出现在你面前。要说容易造成波动的情况,其实还是自己有时候太过于在意人生中出现的变量,但你的职业生涯里可能会产生的好的变量或者坏的变量。比如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第一次在国内做个展的时候,就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虽然说在国外也做过几次个展,但是在国内毕竟还算是一个新鲜的面孔。类似这样的事件都会给我造成阶段性的动荡,那种动荡就会波及到展览之后的一段时间,状态没办法调整回来,不管它的反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即使是好的,反而可能它带来的波动会更大,因为太刺激了。所以我会花时间慢慢去消化这种东西给我带来的影响。
AI:你接下来会不会继续顺着那些好的反馈创作?
傅斯特:不一定。但就好像一个因果链条,不管是好的反馈还是不怎么好的反馈,必定会作用于我们。这个时候如何对它反应,可能就是你看到自我的时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都是自己在工作室里独自完成,然后展览开了,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在看你的成果,就会带来一些另外的问题。但我后来慢慢把自己调整好了,只要这个作品出了工作室就尽量不要太关注之后发生的事情,尽管不容易,但还是进步了很多。
AI:那你现在要面临新的挑战了,因为你在国内,离所有的相关人都更近了。
傅斯特:对,而且下次会是在北京做个展,以前都在上海、在法国。北京是第一次。
AI:换画廊的话,藏家也会换吗?
傅斯特:据说北京的藏家跟上海的藏家不太一样,可能也会面临一个新的群体。
AI:好像口味差别还蛮大的。
傅斯特:都是这么说的。
AI:你一般是怎么处理和消化你收到的反馈的?
傅斯特:我收到反馈以后,我会去想这反馈对我的创作来说是有用的吗,是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上的反馈,还是一个误读,之后我再决定这种反馈是否会对我起作用。其实还是比较少听到不好的反馈,可能别人也不会直接跟我说。
AI:如果有那种更喜欢你以前风格的藏家,在你转变了之后没有继续买的,这算不算反馈?
傅斯特:肯定算,但没有直接聊过只能是靠猜测是这个原因了。我突然想到我前一段得到一个反馈,藏家名字就不提了。他买过我2023和之前的在巴黎那个时期的绘画,然后近一年多没有买过,但他有我好几件作品。他那天见到就问我关于现在的转变,尤其是在跟没顶画廊一起合作以后,他认为我的画可能跟画廊的风格进行了某种整合或是在画廊影响之下产生的。所以他也把这个问题也抛给我了。所以我也会突然会疑惑是否这个系列往前推进的一些状态跟画廊的气质有关系,我可能不能排除这种关系有存在的可能的,但我自己完全可以解释这种变化。因为这个变化不是一个表面的变化,而是内核里面的变化。他会问我一个具体的问题,以前的他会比较喜欢画面里不同的质感,视觉语言更丰富、图像趣味更强,但我现在的画相对来说它更单纯,即使看它的色彩很复杂,或者说形态也很复杂,但它不是质感上和视觉层次上的丰富,它是一个单一的质感,是比较软的。你可以用一些词来归纳,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背景也很单纯。
Gethering
布面油画
120×150厘米
2022
上升之路
布面油画
180×150厘米
2023
Fantome playground 局部
布面油画
230×300厘米
2024
AI:像是给雕塑上色。
傅斯特:是的,我其实有跟他进行这样的沟通。之前我考虑的可能更多是在图像层面上,这个是指某种设计的成分,我很会平衡视觉的和质感上的差异,那种交错在一起的形象如何去产生让观众觉得很有趣的关系。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我工作的重点了,我更往前推进了以后,感兴趣的是在于如何生成一个由自己完全创造出来的完整的东西。当然他的反馈我也收到了,但我也会跟他说现在只是在往前推进而已,也许现在这个状态作为藏家可能会有喜恶,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必要的阶段。
AI:不过这种有特别明确好恶,持续进行系统收藏的藏家其实也不多。
傅斯特:是。但基本上藏家都喜欢好看的东西,这是所有藏家都有的好恶,当然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有的藏家说好看可能不是一般“漂亮”的好看,而是很高级的“好看”,这就是一个审美的事情。但是藏家的好恶没办法考虑那么多,你只能考虑自己的审美,然后继续往前推进。
AI:当你提及“他喜欢好看的画”,是不是本来在这个说法当中,“好看”的定义就是相对窄的。因为如果这个“好看”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好看”,我们为啥还用“好看”这个词?你在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它应该还是指某一种“好看”。
傅斯特:我承认是这样的。在法国,有的人在看作品的时候他如果用了“joli”这个词,可能不是夸赞。法语的“joli”就是pretty,好看。但好看和美这个词还是不一样的,法语的“美”是“beau”,我们说c’est beau和c’est joli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joli,其实不一定是代表好,而可能是不好的。因为是纯好看,但其他方面可能不行,就不一定是高级审美。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国内大家说好看的时候一点思想负担都没有,我听藏家说好看的时候,好像挺随便就会用这个词,而且没有担心这个词是有问题的。
AI:你会把藏家当上帝吗?
傅斯特: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在这之前我都没认识几个藏家。
AI:我发现在今天艺术之外的会发生购买行为的行业,大家都会讲消费者是上帝,但其实没有品牌把消费者真的当上帝,消费者又非常习惯想象自己是上帝,有不少冲突都是这种偏差造成的。
但在艺术圈刚好反过来,没人嘴上讲藏家是上帝,但从行为上看,我会发现只有在艺术界,消费者才是真上帝哈哈哈哈。
傅斯特:所以藏家是真上帝吗?
AI:在艺术界,你花了钱,更能享受一种上帝like的体验,我觉得这比你在奢侈品牌买到vic得到的体验要尊贵多了。你在爱马仕或Chanel花到8位数,能回馈给你任何想象之外的东西吗?礼物刻个首字母?巴黎看场秀?但在艺术界,甚至不只是你要买的这一件艺术品,是可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而且这种东西是很潜移默化的,很有权力感的。
傅斯特:这么说我就有点明白了。尤其当你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藏家时,你就可以影响更广泛的人。
AI:今天这个事也在降级。市场好的时候只有那些有影响力的藏家才能施加影响,今天的话,对很多年轻的艺术家而言,有人买就已经可以产生影响了,大部分的个展都卖不光了。
傅斯特:对,我听说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AI:不景气。
傅斯特:有没有那种个别的、比较火的、性价比高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好的?比如说你采访过的,一开始系数很低什么的,我纯属好奇。
AI:我倒真没有想过“性价比”这种归因,或者说没有我听到的案例是被归因为“性价比”的。讲实话,我采访过的系数高的也不会太高,主要还是年轻艺术家,不太有系数超过800的。其实在非蓝筹画廊里,每家总共也没几个能超过800的。
傅斯特:对,这种挺少的。
AI:在处在画廊解散的那个余波当中,你有几个月没有创作吗?
傅斯特:其实还行,大概从4月中到6月初,我画了两三张画,感觉都不太对,可能客观上跟我没有自己的工作室有关系,是在一个朋友借我的一个地儿工作,感觉没有什么归属感。各种因素都有,跟画廊也有一定关系,我会思考。因为你跟一个画廊合作久了以后,你会认为它不管怎样都接得住你,你可以再大胆地往前推一推自己的创作,这是跟画廊的这种长期合作产生的信任,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你会觉得它会接受你的变化,而且它会想办法去把这种变化介绍给别人,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顾虑。
但现在它没有了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个相对安全、相对被保护的状态没有了,你需要找一个新的合作,而这完全是一个未知状态。你不知道未来的这些状况会怎么样,创作往前走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底气,这是一个挺现实的事儿。从所谓的“卖相”,或者是不是被别人喜欢这种层面上,我觉得总体上来讲,在我跟没顶合作的这两年里,我的绘画应该不是一个越来越讨人喜欢的状态,而是一个捉摸不定的状态,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它变化的核心不是为了考虑大家口味的变化,而是考虑我自己在作品推进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变化。所以画廊的稳定性也挺重要的,对我来讲。
AI:你提到有藏家察觉到你的变化,并且说你有朝画廊整体的风格靠近。
我比较好奇这种结果是怎么达成的。首先一个画廊的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其次这个风格是如何能影响到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
傅斯特:我相信你这个问题要是抛给不同的艺术家,他们都会给你这样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你会跟你长期合作的画廊,至少在某种层面上进行一个整合,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
AI:对,但这个结果你如果仔细想想,它其实是有点超出我们心里对“理想世界”认知的一个结果。我给你个参照,央美不同的工作室出来的学生,比如三工,他们的风格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三工出来的,因为他们在那边接受教育,有一个影响力很大也愿意施加影响力的老师。但画廊的艺术家不存在这个因素,所以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达成的呢?
傅斯特:给你打个比方,没顶和别的画廊不太一样,它的画廊的调性非常强,也因为画廊老板是艺术家,而且态度特别明确,有他自己喜欢的艺术类型。虽然说每个画廊的老板可能都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好恶判断的,但是可能他的口味相对集中一些。
AI:这是在你被选择之后,合作之后才发现的,还是之前就知道?
傅斯特:其实之前不了解。2022年的时候画廊来找我,但我挺意外这家我从没想过的画廊会找我,而且很快我就知道他们有长期合作的意思。事后我才知道是一个在巴黎有一面之缘的策展人推的。我当时的风格和没顶乍一看好像是不太合的。但后来我的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比当时更适合没顶画廊,这就是一种气质上的接近。老实说,我还提醒自己不要往没顶口味上靠,因为我看到没顶其他的绘画类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观念绘画,有的甚至用助手来帮他们完成。所以我肯定有一部分是融不进去的。
AI:融不进去是你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有些人在艺术上没有共识,仍然可以正常地聊天交往。
傅斯特:我其实可以跟不同类型的艺术家聊天,我可以欣赏跟我非常不同类的艺术。
AI:但你能感觉一旦跟他聊了,他的影响力就会无法抵挡地扑过来,像个黑洞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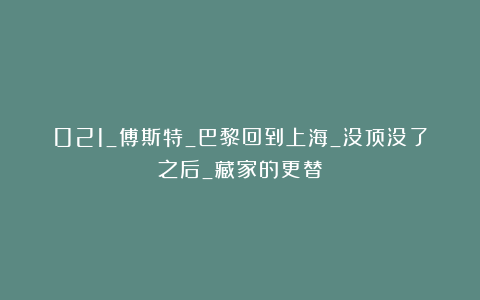
傅斯特:其实就是我也了解自己,毕竟不是初出茅庐了,知道自己的艺术观,当然也明白从底层上不是一体的,所以可以保持欣赏,也没必要什么都聊、什么都要达成彻底一致。
AI:基本上就是听话或者不听话的区别,它并不是一个讨论。
傅斯特:有点这个感觉。
AI:我对圈子里的大佬人物并没有很多了解,但在想象之中,我会觉得那样的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能成功的概率还蛮大的,尤其我觉得有些年轻艺术家如果甘愿做傀儡,听他们的还蛮容易能出来。
傅斯特:我现在觉得没顶还挺尊重我的,他们没有试图要改变我。
AI:但没顶自己先散了,如果真的跟你合作3年、4年、5年之后,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的,可能还是得散。
傅斯特: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AI:但是外界都能感觉到你是有去靠近画廊的某种气质的?
傅斯特: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还认为我在拉开距离。的确,我2023在没顶第一次个展的作品挺有数字、虚拟感的视觉。也许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拉过去了一些而不自知,我后来就往回拉,但可能往回拉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我其实一直都有意识地不要被吸进去,但旁人的视角可能比较客观,我自己倒一段时间以来看不太清。
其实我本来想让你年底或者是几个月以后过来聊一聊,有针对性地聊一聊作品,因为现在我又处于一个新阶段开始前的状态。
AI:等你工作室作品更多了之后,我可以再跟你聊一次。
傅斯特:对,你今天来咱们就聊一聊,反正能聊出什么就算什么。
AI:对,这至少代表了你这个阶段的一个状态。
傅斯特:是。我这两天也看了你们一两篇新的采访,我觉得挖得还挺深的,挺有意思,你的问题还是蛮敏感的。
AI:我不知道是不是敏感,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没有太多顾虑,很敢上。
傅斯特:我发现你观察人会有特别“冷眼旁观”的一种敏锐。
AI:冷吗?
傅斯特:对,有时候会感受到。因为你采访的人太多,所以里面好像有一种很细的分辨,我会察觉到一些非常细小的东西,从他的语言之间能判断出一些东西来。我在采访里头听出来这种东西,比如你甚至会提到过去的某一个人,恰好我又看到过这篇,就很有意思。
AI:其实最初我有试过带导语的版本,也有试过把它做一个编辑感更强、有主线的版本,最后都觉得不太对,其实最后决定发布的是一个最极端的版本,它非常松散。
我其实接到了蛮多反馈的,当然大家是关心我才给我反馈。
傅斯特:一般来说是正面反馈,还是提问题?
AI:他们会给我建议,有人说你应该多放作品,或者说你至少应该编一编顺序,因为他们发现每一篇都很慢热,因为聊天也是要热起来的。基本上前面三四千字过了才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较juicy的东西都是从中部才开始。
最近我特别喜欢问别人会怎么样面对或处理这些反馈,因为我好像没有一个一贯的方法,我目前没听取过建议。
傅斯特:关于“反馈”我刚才怎么回答的?
AI:你刚才没回答。
傅斯特:我没回答吗?
AI:对,你刚才只是回答了你接没接受反馈,咱们就转向了关于具体藏家的聊天。
傅斯特:我后来说了我好像很少接受到直接的反馈,所以没有去想,我想再认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关于“反馈”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怎么去面对“反馈”,可能是你找到自己认识自己的那个时刻。
AI:可以再展开一点?我好像能理解到一些。
傅斯特:面对反馈,怎么做反应,这是个很细致的事儿。它体现了你自己,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如何面对它的第一反应,然后是心态,你是否觉得它有用?或者你即使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但可能你仍然想要坚持自己的风格,或者试图想要做折中处理。这个过程你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极端的人,还是一个有步调的人,你可能需要慢慢在折中状态下向前推进,追求一种求稳的状态。再或者还是说要一决胜负,用自己非常极端的方式坚持原来的纯粹的想法,而不在意他们给你提的那些所谓的意见。我觉得每个人提的意见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但它是不是你原来的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
AI:按照这个逻辑,反而需要更多得到反馈,得到的越多才越成立,你需要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把真实的你给挤压出来。
傅斯特:如果我假设这个“反馈”是我自己的创作的话,我只能回忆一下过去了,因为现在的我可能没法判断,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反馈。
AI:是说最近这个阶段吗?
傅斯特:现在这个阶段我没怎么遇到过别人来讨论作品,那天开幕上我也跟大家聊了聊,大部分都是在介绍自己的作品是怎么工作的,什么状态下产生的之类的,可能有一些反馈,但没有聊得特别深入,所以我也不太好做判断。
但我会想起来,以前我在巴黎早期的时候,做第一次第二次个展的时候收到的反馈,其中不乏正面和负面各种,但我做了综合判断最终在2018年以后选择了转型。转型主要是内在的声音占了主导,我当时感觉到自己那个系列走到尽头了,让我自己感到乏味了。我在那些年收到的所有反馈在其中都起到了帮助我判断、做决定的参照。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翻过我以前更早的作品。
AI:没有很系统地看过,但我有看你工作室的Ins账号。
傅斯特:我2014年在法国的里尔美院毕业,我当年就做了第一次个展,在法国画廊Paris- B,当时叫Paris-Beijing,从那个时候合作一直到现在。但是画廊目前情况有点复杂,题外话。反正那一年算是已经直接从毕业状态进入了职业艺术家的状态,但这一路也是坎坎坷坷吧。2014年的时候我29岁,我22岁就到了法国,大学本科毕业2006年我就到了法国,但是我前面那些年是挺苦的,我不是一个规划性特别强的人。在不断飘荡的状态里慢慢进入到了一个学习的状态,从学习状态又去过渡到职业艺术家的状态。
AI:你是在做职业艺术家之前就结婚了的,还是之后才结婚?
傅斯特:我是17年结婚的,但我14年毕业的那一年已经跟我老婆在一起了。因为我最早做个展的时候,那一年画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个系列叫Politician,给你看,它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单色、晦暗的状态,跟现在就不像一个人画的。
AI:是的。
床,吸烟的男人
纸上混合媒介
110×70厘米
2014
Politician 7
纸上混合媒介
100×140厘米
2014
傅斯特:可以说是一个挺悲观、不安的视角。
AI:我倒觉得那个时候的画,跟我现在眼前人的气质更贴近一点。
傅斯特:我懂你意思。我这个人有两面性,表面有点严肃,但内在却是个天真和乐观的人。
那个时期画的内容大概是那种欧洲的洛可可和巴洛克的室内装饰,比如卧室或是这种带纱的床,有点私密的一个状态,但是又插入了人,他是一个特定的状态,藏在里面,有一种悬疑和让人不安的气质,都是藏在后面,非常隐蔽的状态。
AI:这些人感觉应该是来自于具体图像,像新闻图片。
傅斯特:是的,在新闻图片里面,比如议会里面的一些西方政客互相打架的状态,就会把它拿出来用,虚构到一个情景里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情节暗示的。
AI:有没有这个时期收你的画的人,到现在也会收的。
傅斯特:据我所知好像不多。
AI:因为我看起来这两个时期基本没有关系。
傅斯特:对,但中间还有另外一次过渡,它一直在变化,这是最早的一个个展。我再给你看第二次在法国的个展,基本上是这个系列的,这个时候开始有色彩了,但它的空间变成了一种室内室外交叉的空间,其实我认为这种描绘室内室外空间的形式从Hopper或更早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也还有人在画这种带有心理悬疑的画。
客厅
布面丙烯 三联
180×240厘米
2017
Interior
布面丙烯
120×150厘米
2016
AI:感觉这种可能是在今天也会好卖的,会更接近于你说的“好看”。
傅斯特:可能吧,不知道。当时这个系列开始的时候受到大卫林奇的电影场景的启发,那种氛围。一直到今天,他都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不光是他的电影或某个作品,而是他作为人的状态是我最喜欢的,是最贴近自己内心的,跟内心直觉去走的。
再后来,我就决定要放弃这个形式了,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些反馈,它们对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有另外一部分在起作用,就是我自己内在的需求。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它决定了我现在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作品会截然不同的原因也跟我看世界的方式有关。
AI:你那个时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引发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傅斯特: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从前的我经常会体会、感受到独自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孤立无助”,有一种非常不安定的感觉。而且这个世界实在让我很迷惑,尤其是在国外,又是一个局外人的状态,始终体会到人跟世界的这种关系,你会一直在看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又让你感到很不安,一直在咀嚼人和外在环境的一种关系。我那个时候的作品也呈现了这种关系,这种氛围。就是一种室内的氛围,但它没有办法让你觉得安全,这个世界本身又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所以它有一种困惑在里头。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一些发生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巨大的压迫感。
但后来,经历了一些打磨,比如人生的低谷,很难说是某一个标志性事件,很多事件依次发生,使我逐渐转向内在去思考自我和世界的整体关系。从对立的关系转变成更和谐和连接的感觉。
AI: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帮我具体展开一下或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吗?你讲到跟世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我发现我很难建立起来,我好像只能感受到我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世界对我而言是抽象的,想更具体地了解你是怎么感知到这种关系的?
傅斯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怕人的性格,现在可能痕迹变得不明显,但我从小对于陌生人,对跟任何他者接触都会有一种距离感,会有一种隔绝感。我会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外在于我的一个笼统印象,可能对你来讲这就不是一个问题。
AI:对,因为我听到你这样描述很感兴趣,但确实难以感受到,所以希望你能描述得再具体一点。
傅斯特:我觉得可能就是人和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内在的感受,我回想起我学前班的时候,有一个时刻我还保留着记忆。我觉得人生可能有些这样的时刻,尤其包括童年的时候,比玩得开心的时刻更让你印象深刻,那种时刻我意识到了我和世界的关系,所谓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于认知中的小孩来说,朦胧的觉得世界是因为“我”而存在和有意义,这是儿童的“唯我论”,但很快进入别人也是我,都是“我”。那么意味着我自己肯定不是世界的中心和原因。我杵在教室门口,想着“我”是什么。那种感觉一个小孩难以用用语言表述,只是有种陌生感,我现在去描述就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就是任何的人和事还有世界都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作为一个整体对立于“我”。我这种跟世界疏离甚至对立的心理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我出国的早期阶段。
AI:我可能能体会一半吧。听了你的描述,我确定我从没有到达过那种状态,但同时我想到了可参照的状态:就是我在极端情况之下,会拽一个人进来到我这边,我会界定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跟那个人是在这一边,世界的其它部分在另一边,而且我都不用那个人同意,也不用跟他确认是不是跟我一边的,我就这样在心里决定了。所以我大概知道你的感觉,但“我这边”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过。
傅斯特:对,这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事儿了,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你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AI:我倒觉得它不是一个接不接受的问题,我心里清楚,这个人是我没经过他的允许就把他拉过来的,只是我的认知。
傅斯特:所以我说是潜意识,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如何发生,但它就发生了。
AI:对吧,所以我大概懂你的那个状态,差别只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过。
傅斯特:他会帮助你来对抗这些困难的事情吗?
AI: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处、很困难的人,如果一个人只希望一切都很顺滑或舒适的话,他是不会把我纳入他的圈子之内的。会把我拉进去的人都是那种“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人,可能他们也想要惹惹事儿,或想要多经历一点吧,可能更多是把我当一个素材,或者一个奇怪的可以看戏的存在纳入进去的。
傅斯特:我第一次对你的印象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本来我不认识你,但是你一来,最后我们再聊,可能也是一个慢慢的感觉。我发现你其实特别“硌”,你有很多东西,不是那种特别平滑的人,虽然说你没有“硌”我,但我会感觉到你有这个东西在。
AI:有这种东西在,硌不硌到对方是早晚的事儿,不可能永远都不硌。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敏感度,甚至感觉不到硌,那我们也对不上。
傅斯特:或者跟你是属于一类人,他也能完全接受这种状态,也有可能。
AI:嗯,这个是一种前提吧。我想起我的前老板,他做的一些决定,比如当他决定选择我的时候,其实他需要跟很多人做很多解释。所以我回倒推他懂我这种“硌”按你的说法。但除了选择了我这个大决定之外,在具体的日常共事中,我又很确信他不理解我,不管是价值观和品位,我们都南辕北辙。所以可能是有一个更高的东西,超越的力量,不清楚是什么把我们俩粘在了一起挺久的。
因为这些很玄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跟他的关系,跟他的链接就像是我的一个底线似的,很确信这个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断的。而且互相折磨互相抱怨的状态一直存在,这关系也没有真的破,我一直感到安全,就是世界的另一边跟我们没啥关系的安全。所以这次的破裂对我来讲其实挺毁灭的,我觉得我没有可以相信的事儿了。
傅斯特:至今对你来讲还是难以置信,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是吧?
AI: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在录音这件事,以前采访的时候进行录音,我会更多替对方考虑,担心对方会不自在。但在那个关系破裂之后,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变了,我感觉不管对面是谁,我都是两人之中更没安全感的一个,我脑子里全是关于我自己的信任问题,这个录下来了,我的风险更大,对方风险没我大。
傅斯特:这个事件对你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
AI:对,我以前跟别人的关系不太需要验证,但现在我觉得一切都需要验证,而且当它需要被验证的时候,就会发现什么都靠不住,比如说那些不必要的站队和各种背刺,这种事情每天在发生,我都懵了。
傅斯特: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大事件,而且在现实中,还涉及到工作之间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它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又跟你的工作混在一起。
AI:对。因为其实更明智或对自己更好的方法,应该是逃开,很干净地逃开,而不是回来继续和之前差不多的事业。但我之前尝试去度假,蛮长时间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效的。
傅斯特:你上次跟我提过你去过禅修中心。
AI:我只去了一次,在巴厘岛待了蛮久,但去禅修只去了一次。不行,没用,我的心是乱的,乱到什么都不行,乱到没办法给任何东西机会进入的状态。当然后来我有想,可能是待得还不够久,应该硬逼自己再待久一点,可能就真的显灵了。
我不知道,我又回来了,我其实也会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我是爱你们这群艺术家吗?我是有责任感吗?责任感明显是可疑的。
后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想。
傅斯特:你这样问自己,你是有答案的吗?
AI:我有说法,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答案。在现实当中别人问我,我会直接说:“我可以不回答吗?如果不回答我们就不能继续的话,那么就别继续。”我一般是这样的,所以我有时候想,如果能不回答别人,那也可以不回答自己。动机这个事儿可以重要,也可以不重要。
傅斯特:这是一种分析、一种排除,还是一种思维上的自己跟自己的游戏?有时候会自己欺骗自己,或给自己一个说法,不管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有时候头脑就需要这种东西,活着总是要寻找意义,做事情,这么做了,但好像不应该这么做,于是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事一旦要发生,你总是要给它找一个说法,对吧?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就像你说的,它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要说,也不一定非得当真。
AI:说到这里,我想知道你在画画的时候,会不会给自己开启一种“游戏”?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机制,每次绘画是要玩一个什么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乐于一直玩游戏吗?还是你会希望你能达到一个忘记游戏的状态,不需要再去考虑转译、逻辑、机制或者什么设定。如果你有一天达到了这种“出神”的状态,你会开心吗还是会在察觉到之后立刻自我约束?
傅斯特:“出神”我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少地依赖一些条件,包括好的图像素材,包括依赖任何东西来刺激自我去产生形式。我希望可以推进到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积淀,或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去做输出,这种东西会真的代表自己真正的内在,代表意识层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那种表达可能越来越简单了,但它一定是越来越深刻的。
我觉得真正好的创造,如果是有价值的,一定首先是发自于自己内在的、对自己有效的东西,它才能达到其他人内在的共鸣。对于一个艺术系统或者对于当代世界来说,艺术肯定也需要关心当下的现实,但对我来讲,我喜欢保持一点距离。我在意超越的层面,所以我的工作越来越向内,在创作里越来越向内,而工作也越来越多面对绘画的基本问题。我试图做的事情都是通过一个个阶段经过折中式的探索来获得更多能力,期望自己最后达到完全扔掉拐杖,独立往前走。
AI:没顶没有散的话,你在那家画廊也不会太长久吧?如果你现在表述的真是你要追求的东西的话。
傅斯特:哈哈,我本以为而且期待会一直长久下去。但命运很难预料。
AI:因为你刚刚讲的追求,其实跟他们相信的那个东西刚好是反着来的。你更直觉更绘画,不太观念。
傅斯特:可能是的。需要把自己跟世界绑得再紧一些,才好抓住时代。
AI:这种绑的感觉,你很确信吗?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一种天赋,你的前画廊老板能跟外面的世界同频,是天生的还是努力要求自己做到的?
傅斯特:这肯定是当代艺术这个体系所需要的能力和敏感度。但我总感觉如果不是ego大的人也是做不了试图干预和介入世界的作品,而我不是一个ego很大的人,我是这样对自己认知的。
AI:我一直默认艺术家的ego都是大的。
傅斯特:ego大小没有好坏,只是特征。艺术家肯定需要ego,或者说利用它。但我不觉得只有大的ego才能做出有个性的作品,都可以的。
AI:如果不以ego为前提,你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傅斯特:它可以是宇宙自身的创造,通过自我流淌出来。
AI:你都觉得宇宙要通过你了,这还不ego吗?
傅斯特:这是一种愿景和努力。需要放下一些没必要的东西。我也没有否认我的ego,我只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做事情不一定是通过ego来表达,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多样性存在的必要。哪怕一个小虫子,它也需要以这种形式来存在。但你至少要接受也许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他不以一种很强的ego为依托,可以以一种越来越放松的状态去吸收,甚至让某种东西通过你,再出来。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定的状态,比如你是一个男性或是女性,你就会具备多一些阳刚气质,或是阴柔气质,都会不一样的。不管ego怎样,你的体质已经决定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了,再加上你的性格等等一些宇宙给你的更复杂的设定。我其实是想说这个问题不用推到极端化,只是一个大小的问题。
AI:你有在做一些那种去掉没顶影响的动作吗?
傅斯特:我都不用刻意去努力就知道我接下来的方向会有一些变化。
AI:当他已经是一个故人的时候,有一些时刻你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某种东西,是因为跟他的羁绊而留下的印记,你心里会不会产生那种怀旧带来的暖暖的感觉啊?
傅斯特:我其实会有这样的感觉。
AI:因为他已经是故人了,所以好像发现了印记,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事儿,确实会有点温暖的感觉,至少过去的时间没有白白过去,它有留下痕迹。
傅斯特:我对没顶没有多少负面的东西,画廊最后这么剧烈的事件带来的这种冲击,也不是谁主观上要对我造成伤害,只是恰好发生,我只是恰好被卷进去了,被波及了。但是这两年跟没顶的合作都一直很好,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过去,这是实话。画廊掌舵的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很互补。其实在这事件之前,我对他俩都有非常正面的看法。徐震有很强烈的个人追求,他的追求不是以赚钱为前提,他是一个有愿景的画廊主和艺术家。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在中国艺术生态里里是一个比较稀有的存在。
AI:之前开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八卦的角度,只是非常想知道这些影响是怎么达成的。
傅斯特:你说的是画廊对艺术家风格的影响?
AI:对。我其实不止问过你一个人,我也会问一些刚美院毕业的人,学校里的影响是怎么达成的。也有一些同一个工作室出来的人,他们并没有很相似,那这种“没有”又是怎么达成的?大家都不太讲得清楚。
傅斯特:可能我只能从个人角度来讲,也有一些巧合的成分。比如我跟没顶合作的时期,刚好是我在看德勒兹哲学的时期,大概是2023年那一次个展,那个时候这个褶子哲学对我的影响是关于弹力塑性那种质感的描述以及语言的运动感像画面一样直接给我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灵感,一个褶子团块如何在流动和运动过程中成为其他的东西,包含物质的褶子以及灵魂的褶子。那种状态就跟我当时的人生阶段的状态有呼应。当时处于上升期,快速向前推进的状态,或者说我在成为某种其他状态的变化过程中,那是一个挺剧烈的时期。我的创作又是比较直觉化的,所以那时期的画确切说不是在表达状态,而是隐秘的投射出我自己的状态。所以它借用了某种质感,借用某些概念,又成为了某种样子,刚好它又是我用软件画出来的草图,又碰上了没顶这种很技术风的设定,这一切都感觉是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产生的。我事后看就是这些影响都有。
AI:是不是人在那种becoming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外面的因素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候?
傅斯特:有可能。
AI:而作为美院学生,不管你在不在那个状态,都得调整到一个becoming的状态。因为你是希望去接受教育和被塑造的,那想被改变的和想要施加影响的就刚好碰上了。
傅斯特:对,碰上了,或者我当时在潜意识里面愿意跟画廊和谐和靠近画廊的整体调性。我现在想来,也许是这样子的。之后出于某种原因,出于我自己推进的自然需求,也出于我可能想要拉开一点距离,需要把绘画感再重新找回来,去掉那些过于光滑的虚拟感。
AI:至少从说法上来讲,你的解释是比较可信的,我觉得它达到了某种逻辑上的真实。
傅斯特:刚才说过的那个有反馈的藏家,就直接问我近期作品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在他看来,他觉得我“没顶化”了,他就直接用了这个词。我当时第一反应会觉得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反馈是一个很直接的反馈。他作为藏家来讲,给了我一个非常直接的反馈,让我看到了自己作品在他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如何对他这个东西做反应,其实是一个缓慢的心理过程,因为像他这样的藏家,就是一个你不能忽视的人。
AI:但你会再去验证一下吗?再问一问别人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只是一个非常个体的感觉?
傅斯特:没想过。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已经接受了,我觉得他的想法应该代表一些人。
AI:所以实际上你的藏家也更替了。
傅斯特: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更替了,有一部分可能接受了我新的作品样貌,有一部分可能没有,或者在保持着观察。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